本子娜十大本子全彩,跨海论汉|美国汉学家艾文贺:“真正的修身在日常生活之中”
- 科技数码
- 2025-11-28 16:32:02
- 1
美国新泽西的一个清晨,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教授在他那间别具一格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我的线上采访。那是一处位于自家地下室角落的小空间——靠近一扇通往户外的小门,门外是一片静谧的湖水。艾文贺教授身着浅绿色衬衫,端坐在书桌前;他身后的墙边,静静伫立着一台除湿机与跑步机。
“我不太确定这能不能算作办公室,”他笑着说,“其实就是地下室的出口处。我在这儿放了张书桌,大部分工作都在这里完成。”

艾文贺教授在接受记者线上采访
最近,他正忙于审读《韩国儒学哲学读本》的终稿,翻译《河南程氏遗书》,并筹备即将到来的讲座。“下个月,我要去西蒙菲莎大学(Simon Fraser)大学做讲座,春天去哥伦比亚大学做讲座。明年秋天,我们会在香港大学访问一段时间,然后去韩国。”他说着。看起来,退休后的他比在职时还要忙碌。不过,他也坦言,尽管行程频繁,他和妻子江虹更喜欢待在新泽西的家中。此前,他们曾在中国香港生活十余年,在韩国也住过两三年。如今,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已长大,女儿已有两个孩子——也就是说,他们已是外祖父母了。外孙一家住在马萨诸塞州,离新泽西并不远。艾文贺教授笑言,如今他最珍惜的,是与家人和朋友共度的时光。
艾文贺教授是国际知名的东亚哲学、伦理学与宗教学学者,曾任乔治城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兼系主任。在加入乔治城大学之前,他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陆军服役,退役后赴斯坦福大学攻读宗教研究与亚洲语言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哲学系和宗教研究系任教,并曾执教于密歇根大学、波士顿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以及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院暨东方哲学院。
他的学术著作丰富,包括《和:东亚关于美德、幸福以及我们如何相互联结的认知》(Oneness: East Asian Conceptions of Virtue, Happiness, and How We Are All Connected)、《儒家传统中的伦理学:孟子与王阳明的思想》(Ethics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The Thoughts of Mencius and Wang Yangming)以及《儒家省思:古老智慧对现代的启迪》(Confucian Reflections: Ancient Wisdom for Modern Times)和《儒家道德修养》(Confucian Moral Self Cultivation)等。此外,他还翻译了多部中国哲学经典,如《道德经》、《孙子兵法》等。
作为阳明学与儒家道德哲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艾文贺教授的《“陆王学派”儒家文献选读》(Readings from the Lu-Wang School of Neo-Confucianism)收录并译介了《传习录》、《大学问》节选及若干论学书信、诗歌,被视为英语世界陆王学派研究的权威之作。
有趣的是,在与我的邮件往来中,艾文贺教授对于“澎湃”这个名字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谦虚地写道:“我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朵小浪花,算不上‘澎湃’。不过,我还是很乐意接受你的采访。”

艾文贺
正在翻译《河南程氏遗书》
澎湃新闻:您这个很好听的中文名字“艾文贺”是怎么来的?
艾文贺:这个名字是我的一位中文老师给我起的。我在斯坦福开始学中文时,他根据我的英文名字的谐音取了“艾文贺”这个名字。我很喜欢,从那以后一直用到现在。这位老师不仅教中文,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书法家。他还为我写了两幅《道德经》的书法作品。“艾”是一种小白花,“文贺”则有“成就”“成功”的意思。我常开玩笑说,我喜欢“艾文贺”,就像我喜欢可口可乐——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像Coca-Cola,既意味深长,又朗朗上口,让人听着心情愉快。
澎湃新闻:您最近在忙些什么?您在邮件里提到,正在翻译《河南程氏遗书》(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言论和著作汇编)。为什么会选择这本书?
艾文贺:我正在等待与他人合著的《韩国儒学哲学读本》(Readings in Korean Confucian Philosophy)的样张。书的封面我们已经定下来了。封面上的“鶴”和“學”两个字在韩语中都读作“hak”(在粤语中发音也差不多),其中带着一点文字游戏的意味。这本书将由哈克特出版社(Hackett Publishing)出版。
与此同时,我也在审阅我独立翻译的《河南程氏遗书》的终稿。这部书篇幅庞大,结构复杂。牛津大学出版社(OUP)将以精装本分两卷出版,之后还会推出简化的平装选编版。此外,我正在撰写一篇关于“新儒学的愤怒”及其对当今动荡世界启示的论文,也在阅读并评论世界各地同事和研究生们的研究成果。
至于为什么选择翻译《河南程氏遗书》,其实我研究程颢和程颐的著作已经很多年了。最初开始研究宋明理学时,我受冯友兰的影响很大。他大概是第一位明确提出程颢、程颐两兄弟在思想成熟阶段的哲学取向各有不同的学者。程颐在哥哥去世后又活了很多年,他们的思想也逐渐出现分歧。当代儒家学者陈来也认为:程颢的思想更接近后来的陆王心学(即陆九渊、王阳明建立发展出的心智之学),而程颐则更启发了朱熹的理学体系。我也赞同这种看法。在着手翻译《河南程氏遗书》时,我原本想参考现有的白话译本,结果惊讶地发现并没有完整的版本,只有一些节选。《河南程氏遗书》已有日文和韩文译本,我也参考了这些版本。我希望这本书不仅能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儒家思想,也能促使东亚学界重新思考儒学传统。
澎湃新闻:我了解到您在中国的香港、韩国的首尔和美国华盛顿特区等地都长期生活过,这些地方的文化和社会差异很大。对您来说,在不同地方生活的体验有哪些不同?
艾文贺:我和妻子在这些地方都生活了多年。更早的时候,我在军队服役,也曾在不少国家待过。我从没觉得在各个国家生活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刚到韩国时,我不会韩语;刚开始学中文时,我的中文也不太好。我的体会是,虽然各地的生活方式不同,但人们的兴趣和愿望是相通的——这正是最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从没因为自己是某个圈子里唯一的白人而感到不自在或格格不入。我总能找到聊得来的人,也会遇到意见不同的人,这和我在美国生活时并没有多大区别。我的妻子叫江虹,她来自中国天津,毕业于南开大学,后来在天津电视台工作。之后,她去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而我当时正好在那里任教。我们就在那里认识、相爱并结了婚。她对学术很有兴趣,也喜欢旅行,还喜欢邀请其他学者到家里做客。她是个很有冒险精神的人——毕竟,她都嫁给了一个外国人,这本身就很有冒险精神的嘛!

艾文贺的妻子江虹
澎湃新闻:哈哈,的确是这样。那您出版了那么多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您的夫人会读您的书吗?
艾文贺:我不太确定她有没有读过我写的任何一本书。也许这正是我们婚姻幸福又长久的秘诀(笑)。我们当然会聊一些我书里探讨的话题——哲学、政治、文学之类的,但她并没有直接参与我的研究。我在读中文文章时,如果遇到不太明白的成语,不去问一位中文母语者那可就太傻了。她不仅懂哲学,还精通文学,尤其擅长诗歌——而那正是我的弱项。所以我经常向她请教这类问题。
“儒学更像是一种个人哲学”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成为一位汉学家的?在您最初决定学中文时,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您对中国了解多少?
艾文贺:我大学时主修数学,同时也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那是1972、1973年,越南战争还在进行。我当时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自己在越南究竟在做些什么。于是我想更深入地了解那片地区的文化。在斯坦福大学,当时并没有开设越南语课程,于是我就选择学习中文,因为我觉得中国文化与越南文化之间存在相通、相关之处。学着学着,我逐渐意识到,人类——不仅仅是美国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源自对其他生命形式缺乏理解和尊重。以越南战争为例,在我看来,那显然是一场内战,而美国的介入完全是帝国主义者的,就像当年英国在美国独立之初对待殖民地的方式一样。我那时就开始反思这一切,而这种反思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环顾世界,我常常感到担忧和失望,因为各国似乎依然没有真正的意愿走到一起。坦率地说,我把很大一部分责任归咎于领导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极其糟糕。作为一名军人(我曾是海军陆战队员),我的目标一直是结束冲突,让人类的精力转向更有意义的事物。但这确实很难。
我的父亲和教父——他们也都是海军陆战队员——在二战结束时曾驻扎在中国青岛(当时,中国和美国并肩作战、共同抗日)。当时那片地区在国民党控制之下,他们与国民党一起接受了日本的投降。他们在那里生活了一年,被那片土地深深吸引,对中国的印象极好。因此,我从小对中国就怀有一种天然的好感。中国拥有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一点让我十分钦佩。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人文学者。也许我能成为一个中等水平的数学家,但我发现,在语言和哲学研究上,我或许能做出更有意义的贡献。
澎湃新闻:大多数学者通常只专注于研究一个国家的儒学,而您同时研究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儒学,原因是什么?
艾文贺:我写的《三股清流》(Three Streams)涵盖了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儒学。在这本书里,我引用了不少日本儒学文献,这些文献多用文言文写成。我退伍后从海军陆战队转入陆军,开始学习韩语,并成为监听员,驻扎韩国近三年。后来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美国汉学家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告诉我,如果想成为严肃的儒学研究者,就必须学日语,于是我又学了四年日语。虽然日语口语不太流利,但我能阅读日文文献。也就是说,我先后学习了中文、韩语和日语。韩语和日语在语法上非常相似——尽管很多韩国人不愿承认这一点。中文则完全不同,属于汉藏语系,而韩语和日语通常被归入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不过,传统东亚文化有一大特点:几乎所有学术著作都用文言文写作。这有点像欧洲的拉丁语——如果你懂拉丁文,就能读懂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地的经典作品。在美国,至少在我读书时,你需要学两到三年的现代汉语课程,而古文课程也用现代汉语讲授。实际上,我的专长是古代汉语,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和教授古代汉语。

《三股清流》,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儒学在这三个国家的影响差异?
艾文贺:我的观察是,现在在中国,儒学受到了重视。但我有点担忧的是,政府参与儒学事务,有时会让情况复杂化。当然,政府支持也有积极作用,它让一些杰出学者得以开展卓越研究,比如我的好友彭国翔,我非常欣赏他的研究。
至于韩国,至少受过教育的人普遍认识到儒学的重要性,并给予大力支持。韩国是唯一一个明确以儒学原则建立政府的国家。我曾在成均馆大学教书,那所学校成立于14世纪,与朝鲜王朝同时期建立。该学校至今依然非常重视儒学研究。
在日本,儒学也有影响力,但普通日本人不一定认为自己是儒家信徒。这与儒、道、佛的性质有关,它们不像一神教那样排他。如果你去中国、韩国或日本的庙宇,可能会看到道教、佛教和儒学的元素并存。比如我们在香港生活时,公寓旁边就有一座大型道教寺庙,但其中有一个殿供奉孔子。高考临近时,家长们会去那里为孩子祈福。我注意到日本的庙宇里佛教寺庙和神道神社总是并排出现,我就问一位日本朋友:“日本人有多少是佛教徒,多少是神道信徒,又有多少是儒家信徒?”他回答:“也许75%是佛教徒,75%是神道信徒,75%是儒家信徒。”我当时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后来我明白了:女儿结婚时去神道神社,亲人去世时去佛教寺庙,而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基本上遵循儒家原则。我的老师曾说:“我工作时是儒家信徒,回到家里是道教徒。”我认为东亚人非常务实,他们能看到每种信仰的价值。这也给我很大启发:我自己不是佛教徒,也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但佛教中的一些思想确实能打动我,使我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有类似感受。我希望人们能够自由探索自己想要的生活,可以学习儒学、佛学或其他思想。
澎湃新闻:那您认为儒学与政府,或者说政治与儒学,最理想的关系模式是什么?
艾文贺:现在很多人在写关于儒学作为政治理论的文章,有的观点比较激进,有的认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民主”,有的则认为它更像“精英政治”(meritocracy)。但我个人并不认为儒学提供了特别有趣的政治哲学。纵观历史,大多数儒家学者其实支持君主制度,而我对君主制并不感兴趣。
我认为,儒学更像是一种个人哲学,尤其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深远。很多儒家学者同时也是佛教徒或道教徒。作为一种公共哲学,它传递的核心理念是: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有幸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应该将自己的能力和知识用于比个人更伟大的事业。如果有机会接受教育,就应当以某种方式进入政府,或通过其他途径服务社会、造福民众。我认为,这正是儒学作为个人伦理哲学的独特贡献。我认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便大多数从事自然科学领域工作,也普遍认为自己的研究应服务于社会和人类。这并不是说一定要“为人民服务”,但核心理念是:我们的工作应当对社会和人类有益。这不仅是儒学传统的一大美德,也是我希望更多人能够理解的价值观。今天,有些非常有才华的人,比如埃隆·马斯克,在道德感方面却相对欠缺,这令人遗憾。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做了些好事,但本可以做得更多。而像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弗伦奇·盖茨这样的人,则是我心中的榜样——他们用自己的财富和能力让世界变得更好。
“出于我个人的情感”翻译《道德经》和《孙子兵法》
澎湃新闻:您写了很多书,能否介绍一下哪些是您最重要的著作?
艾文贺:我在不同阶段、出于不同目的写过很多书。例如,《儒家传统中的伦理学:孟子与王阳明的思想》是基于我的博士论文完成的。在这本书中,我试图理清先秦儒学与明代儒学之间的关系。刚开始研究时,有人认为两者几乎相同,只是明代儒学在先秦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但随着研究深入,我发现两者的关系更像亚里士多德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关系:阿奎那称亚里士多德为“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他的思想,使其哲学具有“亚里士多德式”的特征,但阿奎那是基督徒,是圣人,拥有亚里士多德所没有的美德。亚里士多德从未把谦逊或爱视为美德,而两者碰撞后产生了新的东西,但这种新事物的存在仍依赖于前者。在书中,我也特别展示了佛教对中国哲学和儒学的重要影响。

《儒家传统中的伦理学:孟子与王阳明的思想》,哈克特出版社,2002年3月版
随后,我写了《儒家道德修养》,旨在说明一个核心主题:东亚传统中始终贯穿“修身”理念。这在西方哲学中并不常见。西方哲学强调掌握正确理论就能指导行为,但很少关注“发展自己”的过程。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种理念尤其重要,因为很多人即使知道理论,也不一定能付诸实践。我的博士研究中,最初曾考虑研究刘少奇及其他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家。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借鉴了佛教、范仲淹、孟子和孔子的思想。我虽然不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但其中很多思想是原创且有启发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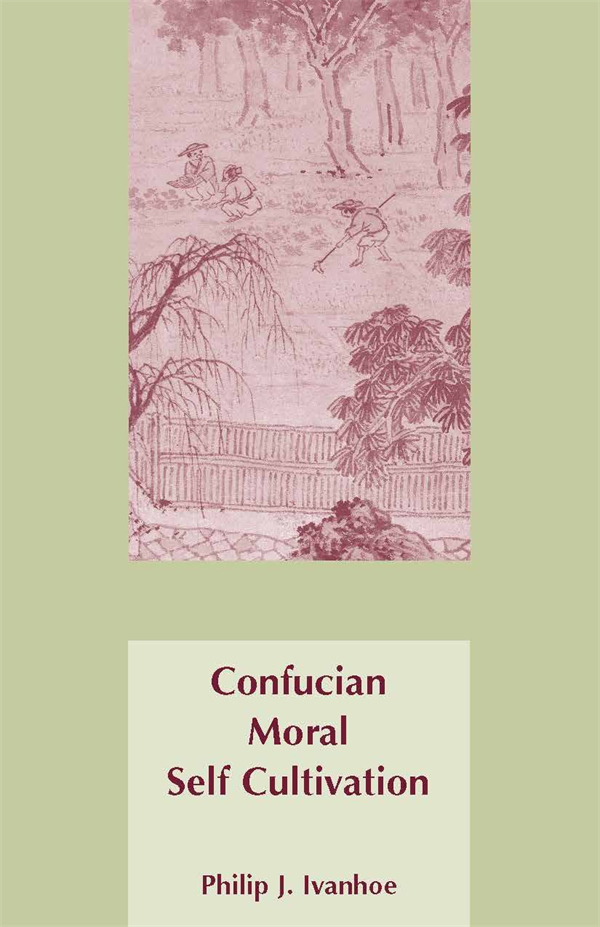
《儒家道德修养》,哈克特出版社,2000年3月版
我还写过关于“和”的书——《和:东亚关于美德、幸福以及我们如何相互联结的认知》。我认为“一体”是东亚思想中的重要主题:我们如何与他人、其他生命以及万物相联结。此外,《儒家省思:古老智慧对现代的启迪》也很受读者欢迎,我希望通过它让更多人了解我对儒学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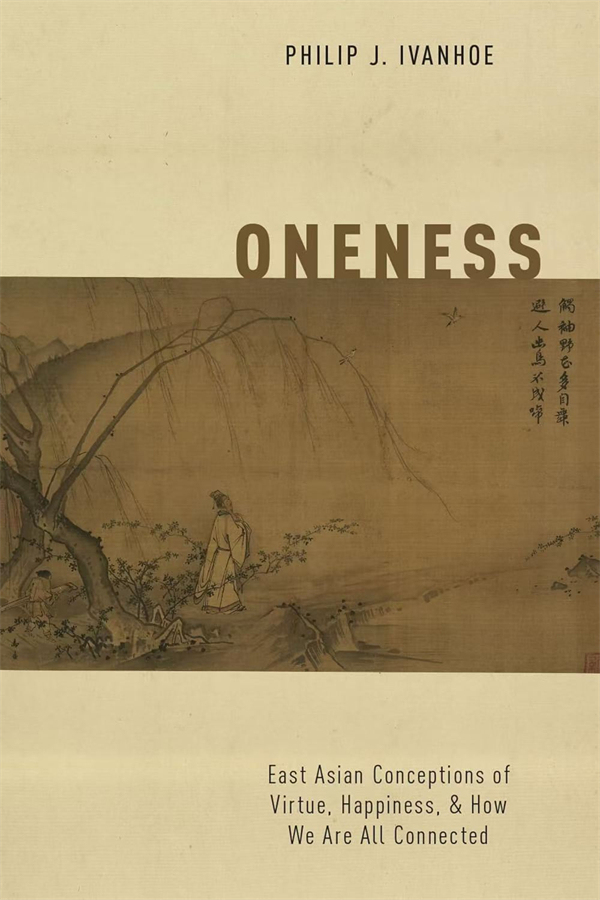
《和:东亚关于美德、幸福以及我们如何相互联结的认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儒家省思:古老智慧对现代的启迪》,劳特利奇出版社,2013年6月版
随着年龄增长,我发现自己更擅长翻译,并能清晰阐释某文本的思想。因此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我花了大量时间从事翻译工作,使更多重要著作以英文面世,尤其是那些从未被译介的作品,例如《河南程氏遗书》。我也翻译了《道德经》和《孙子兵法》,翻译这些书是出于我个人的情感——我一直很喜欢它们,并深受其影响。在翻译风格上,我受到汉学家刘殿爵(D. C. Lau)简洁风格的启发——这种风格贴近中文原文,并保留了一定的模糊性。我后来意识到,大多数译者在参考历代注释时,可能会呈现完全不同的解读。例如,如果你参考赵岐的注本翻译《孟子》,再结合朝鲜学者茶山(Dasan)对《孟子》的重要注疏,最终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版本。我希望通过我的翻译,让《道德经》呈现一以贯之的阐释体系。这本书的附录还收录了《道德经》首章,并汇集了六位权威译者对这一章节的不同译法。我想让读者明白,真正深入的翻译与诠释,总是在与历代注释者对话的过程中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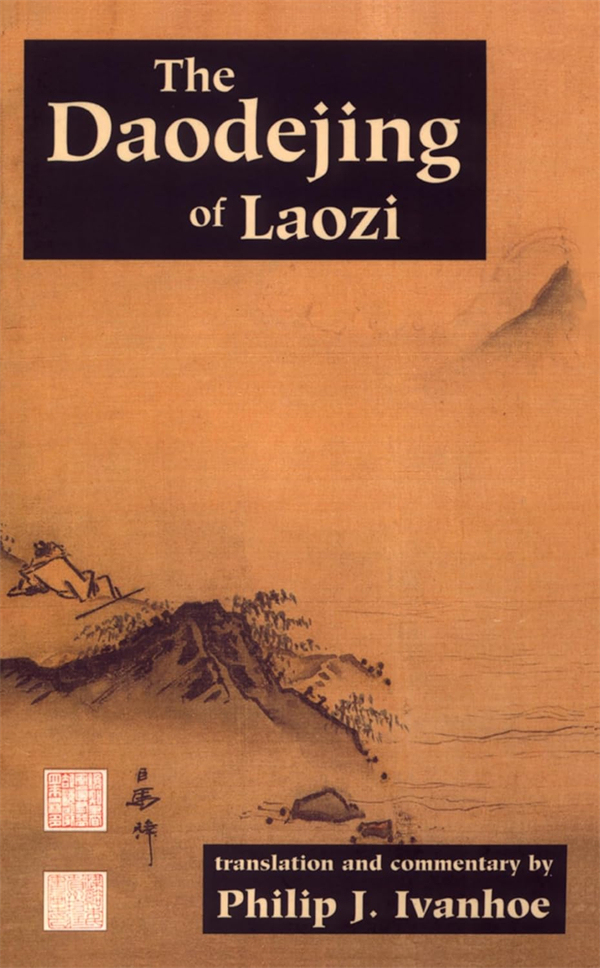
艾文贺翻译的《道德经》,哈克特出版社,2003年8月版
澎湃新闻:在您的学术道路上,哪位导师或学者对您影响最大?
艾文贺:我的博士导师倪德卫对我的影响极为深远。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也让我受益匪浅。在中国学界方面,冯友兰及其著作《中国哲学史》对我的影响尤为深刻。尤其是书中那篇导言,以及他在书中采用的独特写作方式——那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文言文体,几乎接近白话文。他先用现代文体进行分析,然后再引入一大段古文原文,最后进行评注。这看起来很像传统注释体的一种现代变体。对我这样一个同时学习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人来说,这种表达方式极有帮助。此外,像刘殿爵和陈荣捷这样的学者,也在不同阶段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
澎湃新闻:作为一位研究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您所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艾文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避免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去解读中国经典。直到今天,许多西方学者——甚至包括受过西方训练的中国学者——仍倾向于把中国思想看作通向西方哲学体系的“蹒跚尝试”,或者刻意用西方概念来套读它们。比如,有人认为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完全契合,或者认为儒学天然具有女性主义精神。但事实上,连亚里士多德或康德的思想都未必与女性主义相容。如果一个人想成为民主政治理论家,他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深入理解17到20世纪的欧洲政治哲学,而不是试图从儒家传统中寻找预设答案。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悬置既有观念”,真正去倾听、去理解,从他人的立场出发思考。在这方面,我深受德法阐释学传统的影响。我相信,只要足够努力,我们作为人类是能够互相理解、感同身受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和妻子相伴的岁月比你的年龄还长。我们在核心价值观上非常一致,但在很多事情上也常常意见不同。我们的婚姻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当我们有分歧时,我会努力去从她的视角看世界,而她也会尝试从我的立场理解我。如果我们只是各抒己见,就永远无法真正沟通。可惜的是,很多学者在阅读古典著作时,正是这样——他们更多在自说自话,而不是在倾听。
“真正的修身在日常生活之中”
澎湃新闻:是什么吸引您去研究王阳明?您如何评价他,以及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
艾文贺:首先,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我曾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当时总幻想将来能指挥作战部队。而王阳明既是一位将军,指挥过多场重要战役,又是一位思想家与学者——而我自己那时也立志要成为一名学者。王阳明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官员。对我来说,这种结合很迷人。我出身于工人阶级,从未想做一个脱离现实生活的知识分子。王阳明既是伟大的学者与老师,又是勇于担当的行动者,这一点深深吸引了我。此外,他强调“知行合一”,认为道德认知与行动必须统一。杜维明教授曾说,王阳明在某种意义上是儒家的“新教徒”,因为他强调内在的良知,而不必完全依赖经典文本。王阳明写过一首短诗:“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意思是:圣人都只是过眼云烟,真正的老师在于我们内心的良知。我认为这使儒学变得更开放。他让普通人,尤其是商人,也能在生活与事业中追求道德的完善。一个优秀的商人,同样可以成为道德意义上的“圣人”。这也是为什么王阳明在日本特别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许多武士转行经商,从他那里获得启发:你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遵循良知而行。据我观察,在今天中国的某些地方,王阳明思想也在重新兴起,很多成功企业家、餐厅老板组建“阳明学读书会”。我有个学生是香港的商人,他每周都和朋友们一起读王阳明。我讲一个关于王阳明的故事。一位法官问他:“我很喜欢您的哲学,但每天忙于审案,我没时间修身。”王阳明回答:“你在说什么?你审案的时候,就该问自己——是在凭个人好恶判断,还是在追求公正之道?这正是修身的过程。如果你认为只有回家读书才能变得更好,那是不可能的。真正的修身在日常生活之中。”我觉得这是王阳明的巨大魅力之一,也是今天他仍能打动我们的原因。
澎湃新闻:您是让王阳明思想在西方学术界获得广泛理解的重要人物,可以这样认为吗?
艾文贺:杜维明早年写过一本关于王阳明的书,借鉴了《青年路德》的写法,秦家懿(Julia Ching)也写过《求智:王阳明之道》(To Acquire Wisdom: The Way of Wang Yang-ming)。但我关注王阳明的理由稍有不同。一方面,我想探究他与孟子的思想关系。研究越深入,我越觉得:“这个人很有趣。”当然,他受孟子影响,但又有很大的不同。另外,我想弄清楚他思想的结构,以及我们今天能从中获得怎样的启发。别人更多是阐释他,而我尝试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去思考。但必须承认的是,王阳明的一些信念,至少我本人并不完全认同,在现代科学视角下,很多人也不认同。比如,他认为人与生俱来就具备完整的道德知识,而阻碍我们成为好人的是“私欲”。我认为,从经验上看并非如此。人类是进化的动物,有不同的动机和欲望。不过,他的这两个观点确实是对的。第一,与孟子相似,王阳明认为人类天性中确实存在“关怀他人”的倾向——我们有真正的利他性。如果没有这种利他性,人类根本无法生存。我们不是强大的动物,必须依靠彼此的照顾与协作才能以群体形式存续。这种天性虽然并不完整,但却是一个起点。第二,要记得王阳明讲学的对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男性。换句话说,他的学生,就像我在乔治城大学所教的学生一样。你真的认为这些学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吗?现代伦理学的教学方式往往把学生当作“道德空白”的人,好像他们要学康德、休谟或边沁,才知道如何作出道德判断。但事实上,他们早已知道,只是未必能做到。一个成熟的人就已具备了良知。当然,它主要由父母和老师塑造,但大多数人不会真的坐在那里思考:“杀人是不是错的?”“我能骗同事吗?”真正的难题是——如何把这些知道的道理落实在生活中。
澎湃新闻:作为长期研究王阳明的学者,您如何看待“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在当代社会的意义?
艾文贺:王阳明的本意是——道德并不需要庞大的理论体系,而需要更深的自我省思。“致良知”也许可以理解为:行动时更有觉察、更能反省,思考自己为什么这么做,是否心安理得。我在课堂上经常举这个例子:假如你和朋友喝酒后,要开车送他们回家,这时朋友劝你再喝一杯,你可以像康德那样去思考:“我的行为能否成为普遍法则?”你也可以只是简单地想:“我待会要开车送人回家,如果再喝,可能会伤到别人。”这样你就不会靠意志力去克制自己,而是自然地觉得:“安全送他们回家更重要。”你不需要一个抽象的理论,只要把注意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上。这就是“知行合一”的精神。这正是我认为王阳明以及整个东亚思想对当代伦理学的深刻启发所在。当然,道德理论仍然很重要,比如在战场、手术室等极端情境中。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道德:在超市结账时,是否真诚地对收银员说声“你好,谢谢”?是否尊重身边的人?如果能这样做,你也会更喜欢自己,更喜欢自己的生活。
澎湃新闻:有学者认为,正是在西方社会信仰危机与社会发展困境之时,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思想才重新引起学者关注。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艾文贺:确实如此,这也是王阳明在当代中国重新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我妻子为例,她在“文革”末期长大——我就不透露她的年龄了(笑)。她那一代人,其中的很多人仍然相信一种我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美好的一面”的精神,比如那种“我们都是同志、都是兄弟姐妹”的情怀。现在“同志”这个词的含义已经不同了(笑),但那种“人与人之间是兄弟”的理念依然很珍贵。我在美国的黑人文化中也感受到类似的东西——和我年纪相仿的黑人朋友见面时,常以“兄弟”相称。基督徒和伊斯兰教中也有类似的表达。这种情感代表着一种社会理想——彼此尊重、彼此关怀。如今,许多西方人对传统宗教、政府和社会制度失去了信任,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体系,并探索其他传统与文化资源,包括儒家与王阳明的思想。当信仰体系动摇,人们自然会去寻找新的伦理支撑和精神寄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转向其实是一件好事。
“更重要的是学习‘他者’的文化”
澎湃新闻:有人认为,今天的韩国是最接近儒家理想的社会。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艾文贺:如果你在韩国做问卷调查,问人们:“你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佛教徒、儒家信徒、无神论者还是其他”,大约44%的人会说自己是基督徒,类似比例的人是佛教徒,而认为自己是“儒家信徒”的只有约3%。所以,从自我认同来看,儒家信徒的人数非常少。但如果从一个中立的西方观察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韩国社会确实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这不仅体现在民间,也体现在政府层面。韩国宪法甚至规定,政府有责任保护本国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政府设立了与祭祖、扫墓相关的国家节日,包括庆祝六十岁大寿的“花甲节”。孝道仍然被高度重视,对政府的忠诚也很重要。人们期望政府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换句话说,韩国人的日常行为、道德观念和社会关系都深受儒家哲学的深刻影响。我感到,儒家思想在中国也仍然有影响,即便在年轻人中也存在。比如我的学生会称呼我妻子“师母”,把我们视为第二或第三个父母。这种价值观和师生关系中的“仁”与“敬”,非常珍贵。
澎湃新闻:朱熹的理学与王阳明的心学在韩国分别是如何发展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艾文贺:阳明学在日本、韩国、中国的发展路径和文化作用都完全不同。这与历史背景息息相关。高丽王朝把佛教定位国教,朝鲜王朝取而代之后明确以儒学取代佛教。朝鲜王朝建立时,明朝刚灭亡,当时许多人认为明朝的灭亡与王阳明及其追随者有关——他们的思想太“佛系”、太放纵,认为明朝之所以被征服,是因为丢掉了儒家的正统信念。因此,朝鲜王朝的大部分儒家学者认为不能走明朝的老路,必须坚持正统,并选择朱熹理学,压制王阳明心学。而日本的情况几乎相反。阳明学在日本极为流行,受到武士阶层的喜爱——因为武士阶层觉得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非常契合他们的精神——他不是只会写字、弹琴的文人,而是行动派。阳明学甚至影响到作家三岛由纪夫。
澎湃新闻:您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理念是怎样形成的?
艾文贺:过去几年,我在乔治城大学主持了一个研究项目,与几位中国学者合作,探讨“中国传统中存在哪些形式的‘世界主义’思想”,以及这种思想与西方世界主义的差异。我认为,西方关于世界主义的讨论,真正兴起大约是在1994年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发表《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那篇文章之后。但在我看来,西方的世界主义深受康德的影响。努斯鲍姆常说:种族、性别、历史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是理性而有道德的个体——因此要彼此尊重。但我一直对这种说法感到不适。我觉得这并不是我理解的世界主义。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到我家做客,看到墙上挂着中国书画,也注意到我的妻子是中国人,但他们从不问起这些,也不问我们的经历。我就会觉得,他们其实并不真正关心我,甚至某种意义上并不尊重我。我记得很多年前在香港主持一场会议,参会者大多是来自英美的学者。会议开了三天,我最后忍不住说:“我有点失望,你们很多人第一次来香港、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这几天我们在教室里开会,墙上挂着漂亮的书法卷轴,我们还参观了庙宇,但没有一个人问我——那幅书法写的是什么?庙里的器物有什么含义?你们只关心哪里能订制西装、哪里能买到便宜手表。”
我之所以重视世界主义,是因为我一生都在不同文化之间生活和学习。我在一个工人阶级社区长大,那里种族多元——我的祖父母来自东欧,邻居中有意大利人、波多黎各人……我们从不封闭,而是互相了解、交流。我心中的世界主义观念,也受《论语》里一个小故事启发:孔子到庙里参观,不断向人询问各种祭祀礼仪:“那是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等他离开后,庙里的人问:“我以为孔子是大贤人,这些他早该知道,为什么还要问我?”弟子回答:“他当然知道,但他想听听你的想法,他想与你交流。”我觉得这正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世界主义者”。我还记得看过一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电影,片中女主角被称为“世界主义者”。她往来于旧金山、纽约、伦敦、巴黎、上海、东京,每到一地都能说上几句当地语言、结交朋友,并真正了解他人的生活与兴趣。而如今美国学界所谓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常常只是研究美国社会内部的不同族群。这固然有价值,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学习“他者”的文化——比如波斯、印度、中国的文化。我记得在斯坦福大学时,学校计划设立“亚裔美国研究系”,邀请我提建议。我看了方案后表示:我支持这个研究方向,但不支持将其设为独立系所,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他们是亚裔美国人——觉得美国社会有一个“主体”,而亚裔、非裔、拉美裔只是“主菜之外的小配菜”。对我来说,亚裔早已是美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非裔更是从建国之初就参与其中。我们不该把文化“分门别类”,而应该摆脱这种狭隘、封闭的视角。
澎湃新闻:儒家思想对您个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艾文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所受的教育始终提醒我:人生应当服务于比自己更伟大的目标,而家庭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之所以和妻子结婚,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我们对家庭有相似的看法。经营一个成功的家庭,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我从未把这看作“牺牲”。我们有两个孩子,别人常对我说:“你为了孩子牺牲了那么多。”但我从来不这样看。比如,当我和儿子一起玩球,或者带女儿去迪士尼时,我从不会觉得:“啊,我本来可以写一篇论文,现在时间却浪费在这上面。”相反,我会想:他们多快乐啊!那才是真正值得的事。妻子常和我开玩笑说,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几乎熟悉所有儿童电影。我认为,这种以家庭为重的态度正是儒家思想带给我的。此外,儒家思想也让我学会尊重差异——去理解并珍视其他文化,认识到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无法互相取代的多样性。在这方面,我也深受欧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的影响。他和我一样,是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者。我们相信,人类虽然是进化的产物,但不同于河狸或其他动物——人类拥有文化,而文化带来多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因如此,当我听到一些哲学家声称不需要研究印度、波斯或中国哲学,只研究欧洲或英美思想就足够时,我真的很震惊。

艾文贺和外孙
“欧洲人其实早就了解中国”
澎湃新闻:您认为,西方人对儒家文明的哪些部分感到亲近?
艾文贺:首先是家庭。人们往往被“理想的家庭”所吸引,即便他们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的儿子现在读研究生,他说,几乎他所有朋友的父母都离婚了,或者孩子和父母关系紧张。他们对他说:“你爱你的父母,你的父母也爱你;他们来看你时,你们会一起吃饭……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父母是什么感觉。”所以我认为,人们渴望这种生活,这种情感会引起共鸣。
其次是关于“关怀”和“自我修养”的教导,如果以恰当方式呈现,这些内容会打动美国学生。
还有另一点,这不仅是儒家的特点,道家也体现了类似思想。很多年前,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写过一本书《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anism: The Secular as Sacred),意思是在世间本身看到神圣,而不是将神圣寄托于超越世界之外。就像我常教的,有些人寻找“生命的意义”(meaning of life),比如“上帝赋予我意义”或“等我证得涅槃,一切都会有意义”;但也有人关注“生命之中的意义”(meaning in life)。我认同后者。对我来说,意义就是我的家庭、我对妻子的爱、我们共同经历和建设的一切,我与同事一起付出的努力,以及多年的教学,这些事情构成了生活的意义。我不认为死后还能看到意义,所谓“善终”或许是人生最后能完成的一件好事。我见过有人在生命终点平和满足地回顾自己的一生,说“这一切融入一种合一”,这正是我理解的“善终”。还有“合一”。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他年轻时像急流的瀑布,冲过一切;晚年则像河流汇入三角洲,分流灌溉田地,最终融入大海,自己消失,但留下耕耘过的土地。这种感受与中国思想中的“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不谋而合。这种观念对于不信仰超越性宗教的人颇有吸引力。而与此相对的,并非“随心所欲、自私自利”,而是要为更好的社会、更好的世界努力,包括关心自然环境。这正是许多年轻人能产生共鸣的原因。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儒家思想在西方受欢迎的重要因素。
澎湃新闻:西方文明是否从儒家文明中吸收过成果?
艾文贺:有一点非常明确,虽然常被忽略——欧洲人其实早就了解中国,而且印象极深。比如莱布尼茨(Leibniz),他不仅是微积分的发明者之一,也在多个领域有卓越贡献,是个真正的天才。他从耶稣会士的报告中了解到,中国通过考试和才华选拔官员,而在当时的欧洲,如果你不是贵族出身,根本无法担任公职——多么愚蠢的制度啊!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因此都很推崇中国。莱布尼茨甚至写过一本名为《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Discourse on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the Chinese),其中体现了“世俗即神圣”的思想。伏尔泰则强调“有教养的人”,不仅指哲学修养,还包括绘画、诗歌及对世界的敏感,这种理想打动了许多人。从实践来看,尤其是法国知识分子,他们后来改革官僚制度,创立了文官考试制度。毫无疑问,今天西方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的雏形正是受到中国科举启发。我甚至希望美国国会也有类似的考试制度,必须通过才能当选议员。所以,我认为科举制度以及“有教养的人在世俗世界中怀有神圣使命感”的理想,确实对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
澎湃新闻:您认为,儒家思想与西方价值观存在哪些相通性?
艾文贺:我觉得两者之间存在许多重叠和联系,但并非完全一致,也有差异。比如“仁”,常被翻译成“benevolence”(仁慈),我认为更接近“humaneness”(人性、恻隐之心)。这种翻译最初来自一位受杰里米·边沁思想影响的基督教传教士。边沁认为人类具有“天然的仁慈”(natural benevolence),他在《孟子》中看到了类似理念。也就是说,人天生具有仁爱和关怀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成立的。在这方面,某些女性主义思潮与儒家思想非常契合——她们也强调“关怀”或“爱”应为首要美德。关系与关怀的理念非常“中式”,值得深入探索。这也与我关注的实证心理学有关——人确实有同理心,但关键是如何培养它。
我最近读了一位斯坦福心理学家的研究,他通过沉浸式虚拟现实实验——让参与者与他人合作完成任务,从而培养同理心。结果显示,同理心水平显著提高,虽然能持续多久还需进一步研究。这样的实验非常有趣。相比之下,许多破坏性电子游戏可能对同理心发展无益,甚至有害。我绝不会让孩子玩军事类或杀戮类的游戏,比如《侠盗猎车手》,因为战争不是游戏。但如果有更多旨在培养同理心的游戏,或许真的可以帮助人们发展关怀之心。
澎湃新闻:您认为,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世俗化过程中起到哪些作用?
艾文贺:我觉得尼采的看法有道理。基督教长期教导“真理将使你自由”,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这实际上也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并不是纯粹个人化的探究,而是对世界的客观说明。以牛顿为例,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也几乎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天才。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他同时也是虔诚的神学家。他认为研究重力、运动等自然规律,就是在理解上帝的法则。因此,宗教反而激励他去探索世界。不过,正如尼采所指出,基督教最终成为自己的掘墓人:随着科学能力增长,人们开始怀疑奇迹和超自然事件。休谟曾说,即便有大量证据表明奇迹发生过,科学理性仍会寻找其他解释。这就是科学对传统宗教形式的挑战。
澎湃新闻:西方世界通常如何看待“儒家思想推动经济腾飞”这一观点?
艾文贺:关于这个问题,学界有许多不同的理论。但我通常会先提出一个自己多年来在中国也常常强调的观点。大约25年前,我在中国做讲座时,常有人对我说:“哦,你在西方教儒学真好。如今中国经济强大了,西方人不得不重新看待中国了。”我当时就回答说:我当然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感到高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的改革。但我学习中文、爱上中国文化、并深深钦佩它,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前,和财富与国力无关。我是否敬佩一个国家,从不取决于它是否富强。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中国自至少唐代起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有人甚至认为从汉代开始便如此。除了近代那段被列强侵略的痛苦时期外,中国几乎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前列。因此,所谓“中国崛起”,更准确地说其实是“回归常态”——重新回到它在人类文明舞台上本应拥有的地位:一个在人文与科学领域都极具创造力的文化体。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绝非什么全新的现象。至于儒家的作用——我认为它一直都在深层地塑造社会。我并不认同所谓“儒家禁欲主义”的解释,也不同意“儒家重家庭会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它所倡导的强大家庭结构。家庭的力量是人生的根基。我自己出身贫寒,父母几乎一无所有,却白手起家创业,供养三个孩子上学。我们三人后来都上了大学,我成为教授,我的两个姐妹也都事业有成。是什么让我们成功?是家庭的凝聚力。父母把抚养、教育孩子看作头等大事。
其次,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信念:受教育是好事。犹太人也有类似的传统。我有很多犹太朋友,他们一听说你是教授,就会由衷地说一句“太好了”——他们尊重学问,就像尊重财富一样。记得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学经济学的朋友,他和妻子都是银行家。一次聚会上,一个喝醉的人走过来对我说:“你在斯坦福大学教书?你这么聪明,怎么不富有呢?”我回答:“那别人也可以问你——你这么富有,怎么不聪明呢?”(笑)有钱当然好,生活舒适也很好,但人生的真正目标,是成为一个有学问、懂得为人之道的人。那才是真正的成功。我常对孩子们说:如果他们像埃隆·马斯克那样有钱,却成了一个糟糕的人,我会非常失望。
再就是,儒家思想中有一个根本理念,在《大学》等早期经典里就已提出——“反身而诚”。我和妻子常常说,这是我们希望能在美国推广的观念:当出了问题,先反省自己——“我能做什么?”如果你能不断修养自身,你的家庭就会更好;家庭好了,社区就会更好;社区好了,国家也会更好。换句话说,你是在努力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这种思想带来的结果,是更强的社会稳定和更高的政治信任。而政府若要赢得信任,也必须有所作为——以仁心待人,让人民的生活更好。
我在东亚生活多年,印象最深的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地方:那里的人必须缴纳养老保险,这是强制性的;而在美国,这只是可选项,很多人根本不缴,结果年老时一无所有。东亚国家普遍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公立医院、养老体系、社会安全网等。在香港,我们探访过一些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养老院,条件虽然简朴,却干净、安全,老人们有尊严地生活。而在美国,人们常常会说:“你(政府)欠我的,我有权得到这一切。”在我看来,除了不被迫害、不被拷打这样的基本人权之外,没有人“天生有权”获得一切。真正良好的社会,不是建立在“权利索取”的观念上,而是建立在仁心与关怀之上。所以,我认为,儒家思想已经在新加坡、韩国等现代化社会中发挥着深远影响。在那里,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好政府,应该“仁政爱民”;而“仁爱”正是治理的最高境界。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中、西方家庭伦理存在哪些共性?
艾文贺:我想,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社会的人不会偏爱自己的家人——除了某些“病态”的极端时代。除此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爱护家人是理所当然的。我和妻子花钱送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而不是拿去帮别人家的孩子——这根本不需要解释。每个人都会优先照顾自己的家人,这是“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此。我始终认为,家庭之爱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在家庭中没有感受到爱,他的人生往往会很艰难。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那些从小感受到被爱、有依靠的孩子,往往在之后的人生中更加稳定、自信。我们在香港生活时,就买下了现在美国的这栋房子。那时我妻子对我说:“我想在美国买一套房子,这样回美国时,孩子们就有地方住。”我当时觉得没必要,但后来发现那真是个好主意!我当时还说:“那我们买一个湖边小屋吧,退休后住在那里。”她说:“可以,但要有一个女儿的房间,一个儿子的房间,还有我们的卧室和书房。”我说:“亲爱的,那可是四个卧室——太大了吧!”她回答:“是的,但我们需要。孩子们必须知道那里永远是他们的家。”即使我们的女儿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她仍然知道,这里是她永远的家。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因为我自己小时候也有这种安全感。所以,我从不缺乏自信,总觉得可以应对一切。因为我知道有家人的爱与支持。这些观念其实是普遍的,只是表现方式不同。在中国和东亚社会,这种家庭意识更加明显;而在西方,个人主义有时会削弱这种纽带,这一点让我觉得很遗憾。

艾文贺教授和他的家人、亲戚一起过感恩节
(感谢寻梦依为本次采访、稿件提出的宝贵建议。)